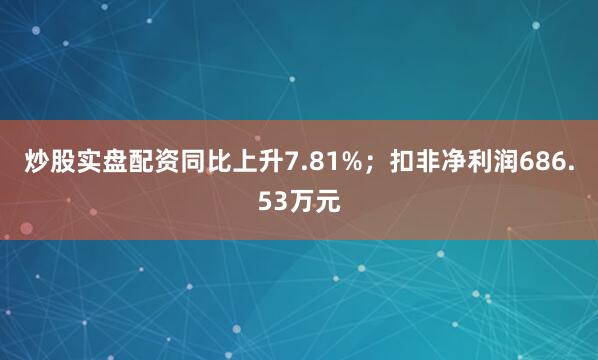1947年10月19日深夜,河北定县清风店。
秋风萧瑟,残月如钩。第三军军部的临时指挥所里,煤油灯忽明忽暗,映照着罗历戎那张刚毅却布满疲惫的脸庞。这位46岁的中将军长,黄埔二期的老资格,此刻正死死盯着作战地图上那个已经被红色箭头包围得密不透风的蓝色方块——那是他的第三军,两万余人的生死,就在这个深秋的夜晚悬于一线。
“军座,”参谋长李铁军推门而入,脸色惨白如纸,“七师的防线已经全部崩溃,敌军主力正从三个方向向我们压来。弟兄们…弟兄们已经三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
罗历戎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炮声隆隆,火光冲天。那是他的部队在做最后的抵抗。他能听见士兵们的呐喊声,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还有那种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辨识出的味道——死亡的味道。
“传令下去,”他的声音异常平静,平静得让李铁军感到一阵寒意,“所有建制打散,以营为单位分散突围。告诉弟兄们,能走一个是一个。”
“军座,您呢?”
罗历戎转过身,目光扫过指挥所里的每一个人。这些跟随他多年的部下,有的是从淞沪会战就在一起的老兄弟,有的是南京保卫战中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的眼神里,有恐惧,有不甘,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绝望的依赖——他们在等待他们的军长做出最后的决定。
“黄埔的军人,”罗历戎的声音突然提高,“没有投降的!”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每个人的心上。是的,黄埔军人没有投降的传统。从东征到北伐,从抗日到现在,多少黄埔同窗战死沙场,但投降?那是对黄埔精神最大的背叛。
然而,窗外的枪声越来越近了。
罗历戎走到墙边,取下挂在那里的指挥刀。这把刀跟随他走过了大半个中国,见证了他从一个四川山村的穷小子成长为国民党的中将军长。刀身上还残留着淞沪会战时溅上的血迹,那是他亲手砍杀日本兵留下的印记。
“军座!”突然,通讯兵跌跌撞撞地冲进来,“东北方向出现缺口!是咱们的警卫营打开的!快走!”
罗历戎看了看表,凌晨三点十五分。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所有人,立即突围!”
指挥所瞬间乱作一团。文件在焚烧,电台在销毁,军官们在匆忙收拾着最重要的东西。罗历戎却站在原地没有动,他的目光落在墙上那张巨大的中国地图上。从广州到南京,从上海到武汉,从重庆到北平,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他走过了大半个中国。而现在,一切都要在这个叫清风店的小地方画上句号了。
“军座,快走啊!”李铁军几乎是在哀求。

罗历戎深吸一口气,最后看了一眼那张地图,转身大步走出指挥所。
02
凌晨的突围是一场噩梦。
罗历戎骑在马上,身边只剩下不到一个连的警卫。他们沿着一条乡间小路疾驰,希望能在天亮前冲出包围圈。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解放军早已在所有可能的突围路线上布下了天罗地网。
“军座,前面有情况!”尖兵的声音充满惊恐。
话音未落,四周突然爆发出密集的枪声。子弹如雨点般从黑暗中射来,罗历戎的坐骑一声悲鸣,前腿一软跪倒在地。他被重重摔在地上,指挥刀脱手飞出,消失在黑暗中。
“保护军座!”
警卫们围成一圈,用身体为他筑起一道屏障。但在解放军的强大火力面前,这道屏障很快就被撕开了口子。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身影倒下,鲜血染红了清晨的露水。
罗历戎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刚才的摔倒让他的右腿传来钻心的疼痛。他知道,可能是骨折了。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出现在他面前,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额头。
“你是罗历戎?”年轻战士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确定。
罗历戎苦笑了一下。他突然想起二十三年前,自己也是这般年轻,满怀激情地走进黄埔军校的大门。那时的他相信,自己将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贡献一生。可是现在,他却倒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下。
“是的,”他说,“我是罗历戎。”
年轻战士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面前这个狼狈不堪的中年人,就是国民党的中将军长。他回头喊道:“报告连长!抓到一个大官!他说他是罗历戎!”
很快,更多的解放军战士围了上来。罗历戎被两个战士架起,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就在被带走的那一刻,他回头看了一眼。晨曦初现,清风店的原野上,到处都是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武器装备,还有那些再也站不起来的士兵。
第三军,这支他亲手带了三年的部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03
被俘后的第一个夜晚,罗历戎被关在一间农家的柴房里。
这间柴房很小,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破旧的板凳。墙角堆着一些干柴,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柴草的味道。透过木板的缝隙,可以看到外面站岗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很年轻,脸上还带着稚气。
罗历戎坐在木板床上,双手抱头。他的脑海里不断重现着被俘的那一刻——当他说出自己名字时,那个年轻战士脸上露出的惊讶表情。是的,他罗历戎,堂堂的国民党中将,黄埔二期的高材生,竟然成了共产党的俘虏。
他想到了他的老师蒋介石。如果校长知道他被俘了,会是什么反应?失望?愤怒?还是会像对待其他被俘将领一样,在公开场合说他“殉国”了?
他想到了他的黄埔同学们。邱清泉、李仙洲、郑洞国…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会怎么看待他这个第一个被俘的中将?会同情?会鄙视?还是会庆幸自己不是第一个?
最让他痛苦的是,他想到了那些死去的部下。三天的战斗,第三军伤亡过半,那些十八九岁的士兵,很多都是刚刚入伍的新兵。他们相信他们的军长,相信国民政府,相信他们是在为国家而战。可是现在,他们都死了,而他们的军长却活着,成了俘虏。
“为什么不让我死在战场上?”罗历戎喃喃自语,泪水第一次模糊了这个硬汉的双眼。
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解放军军官走了进来。他看起来三十多岁,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罗将军,”他说,“我是华北野战军政治部的王干事。我来看看您,有什么需要吗?”
罗历戎抬起头,目光冰冷:“我需要一把枪。”
王干事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罗将军,您这是何必呢?您是抗日名将,打过日本人,这是功劳。现在战争结束了,您可以…”
“住口!”罗历戎突然暴怒,“我罗历戎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你们杀了我吧,我绝不会投降!”
王干事推了推眼镜,平静地说:“罗将军,我们不会杀您的。您好好休息,明天我们要转移了。”
说完,他转身离开,留下罗历戎一个人在黑暗中。
04
第二天清晨,罗历戎被转移到了华北野战军的后方医院。他的右腿确实骨折了,需要治疗。
躺在病床上的日子里,罗历戎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他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从四川渠县的那个贫苦少年,到今天的阶下囚,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想起了1924年的那个夏天,自己怀着满腔热血来到广州,想要报考黄埔军校。那时的广州,到处都是革命的气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深深打动了他,他相信,只有通过武力统一中国,才能让这个古老的国家重新站起来。
他想起了东征和北伐。那时的国共两党还在合作,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冲锋陷阵时的激动,记得第一次击毙敌人时的颤抖,记得第一次看到战友牺牲时的悲痛。

他想起了1927年的那个春天,国共分裂了。他选择了追随蒋介石,不是因为他特别信任蒋,而是因为他觉得,国民党代表着正统,代表着秩序。而共产党?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那套理论太过激进,不适合中国。
然后是抗日战争。这是罗历戎军旅生涯中最骄傲的一段时光。在淞沪会战中,他带领部队与日军血战三个月;在南京保卫战中,他坚守到最后一刻;在武汉会战中,他一次次打退日军的进攻。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为民族而战,为国家而战。
可是抗战胜利后呢?内战爆发了。起初,罗历戎也有过犹豫。打了八年日本人,现在又要打自己人,这算什么?但上级的命令下来了,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他也确实觉得共产党的那一套不行,中国需要的是稳定,是秩序,而不是革命。
可是现在,躺在共产党的医院里,看着那些解放军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罗历戎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这些人,和他想象中的“共匪”完全不一样。他们有纪律,有文化,对俘虏也很人道。最让他惊讶的是,很多解放军战士都能读书写字,而他的第三军里,文盲占了大多数。
“罗将军,该换药了。”一个年轻的女护士走了进来。
罗历戎看着她。这个女孩最多二十岁,脸上还带着稚气,但手法很熟练。她一边给他换药,一边说:“您的腿恢复得不错,再过一个月应该就能下地了。”
“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罗历戎突然问道。
女护士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家是河北农民,解放军来了,分了地,我们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我哥哥参军了,我就当了护士。我们是在为自己打仗,为穷人打仗。”
罗历戎沉默了。为自己打仗,为穷人打仗。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却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出身。他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啊,如果不是靠着一些机缘,他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四川的大山。
05
1948年春天,罗历戎被转移到了华北军区的战俘管理所。这里关押着几百名国民党军官,从少尉到少将都有,而罗历戎是军衔最高的。
管理所设在一个废弃的兵营里,条件虽然简陋,但基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每天三餐,虽然简单,但能吃饱。有固定的学习时间,学习内容主要是时事政治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起初,罗历戎对这些学习极度抵触。每次上课,他都坐在最后排,要么闭目养神,要么望着窗外发呆。负责给他们上课的是一位姓陈的指导员,三十多岁,据说是延安出来的老革命。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陈指导员说,“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
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说是因为外国侵略,有人说是因为军阀混战,有人说是因为教育落后。罗历戎冷笑一声:“因为有你们共产党搞破坏!”
全场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罗历戎。陈指导员却没有生气,反而走到罗历戎面前:“罗将军,您是黄埔出身,读过书,见过世面。您真的认为,中国的贫穷是因为共产党吗?那1927年以前呢?1921年以前呢?”
罗历戎哑口无言。是啊,共产党1921年才成立,可中国的贫穷落后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陈指导员继续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老家在山西,是个佃农。我们一家五口,种着地主家二十亩地,每年收成的七成要交租,剩下的三成还不够吃半年。我十岁那年,闹旱灾,颗粒无收,地主还是要收租。我爹没办法,把我妹妹卖了,换了两袋粮食。可是第二年,我娘还是饿死了。”
他停了停,看着在场的军官们:“各位都是军人,打过不少仗。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士兵为什么打仗?他们大多数都是农民,都有类似的故事。他们参军,有的是被抓壮丁,有的是为了混口饭吃。可是解放军不一样,解放军的战士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因为他们在为自己的土地打仗,为自己的未来打仗。”
罗历戎低下了头。他想起了自己的部队,确实,大部分士兵都是被抓来的壮丁,打起仗来常常一触即溃。而解放军呢?他们的战斗意志为什么那么顽强?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们有信仰?
06
时间一天天过去,罗历戎开始慢慢改变。他开始认真听课,开始看那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开始和其他俘虏军官讨论问题。
最大的转变发生在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管理所组织所有人收听广播。当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罗历戎的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
他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哭。也许是因为中国终于统一了,也许是因为战争终于结束了,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罗将军,您怎么了?”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国民党上校问道。
罗历戎擦了擦眼泪:“没什么,只是…只是想到,中国人不用再打中国人了。”
从那以后,罗历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开始主动参与学习讨论,开始写思想汇报,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他意识到,自己虽然打过日本人,是民族英雄,但在内战中,他确实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听到美国人打到鸭绿江边时,罗历戎激动地找到陈指导员:“让我去朝鲜!我是军人,我懂军事,我可以帮忙!”
陈指导员摇了摇头:“罗将军,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您现在的身份…不过,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贡献力量。”
“什么方式?”
“写。把您的经历写下来,把您所知道的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写下来。这些资料对我们很有价值。”
于是,罗历戎开始写作。他写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写主要将领的特点,写重要战役的得失。这些资料后来都成了研究国民党军事史的重要参考。
07
1952年,罗历戎被转移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里关押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罗历戎在这里遇到了不少老熟人,其中就包括他的黄埔同学。
“老罗,真没想到咱们会在这里见面。”宋希濂苦笑着说。他比罗历戎晚一年被俘,在淮海战役中。

“是啊,”罗历戎说,“当年在黄埔,谁能想到会有今天?”
在功德林的日子里,这些昔日的将军们除了学习,就是相互交流。他们谈论过去的战争,分析失败的原因,也展望未来的中国。慢慢地,大家都认识到,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我们输在哪里?”一次讨论中,杜聿明提出了这个问题。
“输在民心上。”王耀武说,“共产党得民心,我们失民心。”
“不止如此,”罗历戎说,“我们还输在信仰上。我们的士兵不知道为什么打仗,我们的军官只想着升官发财。而共产党呢?他们从上到下都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奋斗。”
这时,一个管理员走进来:“罗历戎,有人来看你。”
罗历戎愣了一下。谁会来看他?他的家人都在台湾,不可能来的。
走进会见室,他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他当年的警卫员小刘。小刘在清风店战役中负伤被俘,后来加入了解放军。
“军长!”小刘一看到罗历戎就哭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罗历戎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主仆二人相拥而泣。
小刘告诉罗历戎,他现在在解放军某部当连长,这次是专门请假来看他的。“军长,我在解放军里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军队。这里官兵平等,没有打骂,没有克扣军饷。我现在明白了,我们以前真的是在给反动派卖命。”
罗历戎点点头:“是啊,我们都明白得太晚了。”
08
1959年,罗历戎已经在战犯管理所度过了12个年头。这一年,他58岁了,两鬓已经斑白。
这些年里,他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变化。管理所经常组织他们外出参观,看工厂,看农村,看学校。每一次参观回来,罗历戎都会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感受。
“今天参观了鞍钢,那规模,那气势,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兵工厂都要大。工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完全不同,他们是在为自己工作,为国家工作。”
“去了一个人民公社,农民们正在修水利。想起我小时候,家乡也闹过旱灾,可是没人组织修水利,只能靠天吃饭。现在不一样了,农民们组织起来了,他们在改变自己的命运。”
“参观了北京大学,看到那么多工农子弟在读书,真是感慨。我们那个时代,穷人家的孩子哪有机会上大学?现在好了,教育不再是富人的专利了。”
1960年国庆前夕,陈指导员找到罗历戎:“老罗,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中央决定特赦一批战犯,你在名单上。”
罗历戎愣住了。特赦?他做梦都没想过这一天会这么快到来。
“我…我真的可以出去了?”
“是的,不过有个条件。你愿意为新中国工作吗?”
罗历戎毫不犹豫地点头:“愿意!我愿意!只要国家需要我,我做什么都愿意!”
1960年11月28日,罗历戎走出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门。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自由的空气,真好。
09
特赦后的罗历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担任文史专员。他的主要工作是撰写历史资料,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提供第一手材料。
刚开始工作时,罗历戎有些不适应。从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变成一个伏案写作的文员,这个转变确实很大。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的意义。
“我写的不是一般的文章,”他对同事说,“我写的是历史,是真相。我要让后人知道,那场战争是怎么打的,为什么国民党会失败,为什么共产党会胜利。”
罗历戎写作非常认真。每写一篇文章,他都要查阅大量资料,力求准确。遇到记忆模糊的地方,他会写信询问当年的战友,不管他们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
他写了《清风店战役亲历记》,详细记录了第三军覆灭的全过程。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历史学者说,这是研究清风店战役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他还写了《我所知道的国民党派系斗争》、《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黄埔军校的教育与训练》等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文笔生动,可读性很强。
1965年,罗历戎受邀到军事科学院做报告,题目是《国民党军队为什么打不过解放军》。台下坐着的都是解放军的中高级军官,其中不少人当年就是他的对手。
“各位同志,”罗历戎开始了他的演讲,“我站在这里,心情很复杂。20年前,我们是敌人;今天,我们是同志。这个转变,不仅是我个人的转变,也是历史的转变。”

他从军事角度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战略失误、战术呆板、官兵关系恶劣、后勤补给混乱等等。但最后,他说:“所有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一支没有人民支持的军队,不管装备多么精良,训练多么有素,最终都会失败。”
报告结束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位解放军将军走上台,紧紧握住罗历戎的手:“罗老,您的报告很精彩,对我们很有启发。”
罗历戎认出了他,正是当年在清风店俘虏他的部队指挥官。两个昔日的对手,如今成了朋友。
10
1970年代,罗历戎的生活相对平静。虽然经历了一些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总的来说,他受到的影响不大。组织上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和年龄,对他还是比较照顾的。
这期间,罗历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写作上。他不仅写历史资料,还开始写回忆录。他想把自己的一生都记录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份完整的历史见证。
1976年,唐山大地震。75岁的罗历戎主动要求去灾区慰问。有人劝他:“罗老,您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
“正因为我年纪大了,更要去,”罗历戎说,“我这辈子,前半生破坏的多,建设的少。现在国家有难,我不能袖手旁观。”
在唐山,罗历戎看到了人民解放军奋不顾身抢救群众的场景。他想起了当年自己的部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恐怕早就作鸟兽散了。而解放军战士们,明知道余震随时可能发生,还是义无反顾地冲进废墟救人。
“这就是人民军队啊,”罗历戎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难怪他们能打败我们。”
11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罗历戎虽然已经77岁高龄,但他的思想却很开放。
“改革好啊,”他说,“中国封闭了这么多年,是该打开国门了。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但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本。”
这一年,罗历戎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写信的是他的儿子,1949年去了台湾,后来又去了美国。信中说,想回来看看父亲。
罗历戎拿着信的手在颤抖。三十年了,他终于有了儿子的消息。
在组织的安排下,父子终于见面了。儿子已经五十多岁,两鬓斑白。看到父亲,他跪下了:“爸,儿子不孝,这么多年没能在您身边。”
罗历戎扶起儿子:“起来,起来。能见面就好,能见面就好。”
儿子在北京住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罗历戎带着儿子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也参观了一些工厂和学校。
“爸,大陆变化真大,”儿子说,“和我们在外面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是啊,”罗历戎说,“新中国成立30年了,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总的来说,国家是在进步的。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儿子临走时,罗历戎送给他一套自己写的文史资料。“带回去给你的孩子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爷爷经历了什么,中国经历了什么。”
12
1983年,罗历戎被特邀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82岁的他,精神依然矍铄。
在政协会议上,罗历戎积极发言,特别是在讨论祖国统一问题时。
“我是从台湾海峡那边过来的人,”他说,“我知道那边很多人的想法。他们不是不想统一,而是有顾虑。我们要耐心,要让他们看到,统一对大家都有好处。”
他还建议,应该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黄埔同学之间的交流。“黄埔是国共两党共同的记忆,从这里入手,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1984年,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罗历戎应邀参加了纪念活动。在会上,他见到了许多老同学,有的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还有的来自海外。
“60年了,”罗历戎在发言中说,“我们这些黄埔老兵,经历了北伐、抗战、内战。我们曾经并肩作战,也曾经兵戎相见。但是今天,我们又坐在一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都是中国人,说明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
他的话引起了强烈共鸣。一位从台湾来的黄埔同学握着他的手说:“老罗,你说得对。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带着遗憾离开。”
13
1988年,罗历戎87岁了。这一年,他再次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虽然年事已高,但罗历戎依然坚持参加政协的活动。他特别关心教育问题。
“国家要发展,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培养关键在教育,”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这一生,前半生糊涂,就是因为书读得少,眼界窄。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多读书,读好书。”
他还经常到学校去做报告,给年轻人讲历史。每次讲完,都有学生问他:“罗爷爷,您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罗历戎总是这样回答:“历史不能假设。我不后悔,因为那些经历让我最终认识到了真理。我只是遗憾,认识得太晚了。你们这一代人很幸运,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你们要珍惜,要努力,要为国家做贡献。”
1990年,罗历戎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医生诊断是心脏病,建议他住院治疗。

躺在病床上,罗历戎还在坚持写作。他要把回忆录写完,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我这一生,走了很多弯路,”他对来看望他的人说,“但最终还是走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我要把这些都写下来,让后人引以为戒。”
14
1991年春天,罗历戎的病情恶化了。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再去一次清风店。
家人和医生都反对,觉得他的身体承受不了长途旅行。但罗历戎坚持:“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想再去看看。”
在各方的安排下,罗历戎终于回到了清风店。44年过去了,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样。当年的战场变成了农田,当年的废墟上建起了新房。
站在当年被俘的地方,罗历戎老泪纵横。陪同的人问他:“罗老,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那些死去的人,”罗历戎说,“不管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为了各自的信仰而战,最终都成了历史的尘埃。而我,一个失败者,却活了下来,还活了这么久。这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来见证历史,记录历史。”
回到北京后不久,罗历戎就住进了医院。他知道,这一次,他真的要走了。
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床前:“我这一生,前半生糊涂,后半生清醒。我最大的遗憾,是认识真理太晚了。你要记住,人不能和历史潮流对抗,不能和人民对抗。”
1991年8月15日,罗历戎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他的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有他的老战友,有他的同事,有他帮助过的年轻学者,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普通人。
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悼词中说:“罗历戎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他从一个旧军人转变为新中国的建设者,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最终获得了新生。他留下的文史资料,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宝贵财富。”
罗历戎去世后,他的回忆录《从黄埔到政协——我的九十年》出版了。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他的一生,特别是从被俘到特赦再到新生的心路历程。书的扉页上,印着他的一句话:
“我用前半生犯错,用后半生醒悟。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希望能早一点站在人民这一边。”
尾声
2017年,清风店战役70周年。当地政府在战役旧址建立了一个纪念馆。馆里有一个特别的展厅,专门介绍罗历戎。
展厅里陈列着罗历戎的照片、手稿、日记,还有他获得的特赦证书。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墙,上面刻着他说过的一句话:
“一个人可以打败仗,但不能打败自己的良心。我用了13年才明白,真正的胜利不是征服别人,而是征服自己的偏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一个参观的年轻人问讲解员:“他后来真的改变了吗?”
讲解员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说:“我是罗历戎的学生,跟了他十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不仅改变了,而且改变得很彻底。他用自己的后半生,诠释了什么叫凤凰涅槃,什么叫浪子回头。”
年轻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走出纪念馆,阳光正好。清风店的原野上,麦浪滚滚,一片金黄。那场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而罗历戎的故事,却依然在提醒着人们:
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虽然渺小,但并非毫无意义。认识真理,永远不会太晚。
站在人民一边,永远是正确的选择。
【参考资料来源】
《清风店战役史》,军事科学出版社《罗历戎回忆录》手稿,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国民党高级将领传》,中华书局《功德林改造纪实》,人民出版社《黄埔军校史料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华北野战军战史档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明道配资-明道配资官网-股票低息配资-股票配资大盘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中国股市杠杆也沿着长江两岸传入中国
- 下一篇:没有了